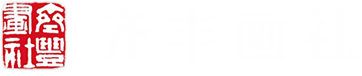于希宁

于希宁:(1913—2007) 山东潍县人。历任山东师范学院美术专修科、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教授、副院长、名誉院长,美协山东分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五届 、六届省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永不忘却的惦念——沈光伟谈于希宁的艺术人生
阴澍雨(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以下简称阴): 沈老师,您是于希宁先生的学生,也是他的亲属,现在又作为学者来研究于老的艺术,我想您在长期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肯定对于老的艺术有更深的理解。我们了解到早年于老是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的,受到俞剑华、潘天寿、黄宾虹这些老先生的影响,让您来谈一下,早年于老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他的艺术渊源如何?
沈光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以下简称沈):于老的艺术,应该是从他所受到的地域文化影响开始,后来到了新华艺专才受到老师的影响。于老出生在潍坊,这个地方传统文化底蕴很厚,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大收藏家陈介祺,仅收藏的秦玺汉印就有上万方,其收藏古印的二层楼房就称作“万印楼”。于老真正走上艺术的道路应该是从学习篆刻开始,那时他年龄还很小,现在能看到的于老的篆刻很多是上大学以前刻的,非常精彩。他早接触的《十钟山房印举》都是原拓,是从陈介祺的藏印中直接打下来,反复研习临摹,从中体会秦玺汉印的古朴大气和隽永灵秀之美,黄宾虹曾给他画的白梅题字:“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画,平寿有道,深明篆刻,此帧得古籀遗意矣。”平寿就是指潍坊,古称平寿,黄宾虹说他那时对篆刻就极精通,画中能透出对篆刻意味的深层理解,是对于希宁很高的褒奖,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陈介祺跟于家是隔壁邻居,陈介祺家的后院就连着于老家的后院,那时候潍坊文人很多,他学画的时代,他的师辈像丁东斋、刘秩东都是水平很高的人。于老也画点西画,画点速写,那时候的西画老师叫张眺,就租住在于家过道里面,张眺后来在上海搞新文化运动,也是李可染的老师。因为潍坊这个地方文化底蕴厚、艺术氛围好,山东早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人很多出在这里。于老不是早的,比于老还早的是徐培基,他是1929年入校,毕业后在新华艺专任教,于老是1933年,还有郭味蕖、陈立先、陈寿荣等。他们先后到上海和北京求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县城里面,有这么多人在大学读书学美术,在是很少见的。

1935年,新华艺专同学旅行写生时合影。(左一为于希宁)
我见到于老早的一本画册是1936年珂罗版印刷的,就是当时潍坊的一个社团——同志画社出版的。于老的启蒙老师、同志画社的发起人丁东斋先生策划,印得很精美,选印的大部分是写生的白描稿,而且由这个社团自己的发行渠道——学生用品营业部来营销。1936年于老23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学子,在30年代就能出版个人画册,可见当时潍坊文风的昌盛。他这一代人学画的经历、画画的路子、求学时所接受的艺术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他们骨子里的传统文化根基,是十分牢固的,同时又接受了一些西学东渐的艺术思想,从而思想上又是非常兼容和开放的,黄宾虹、俞剑华也是中西兼通的,但是以中式教育为主。

《丹心铁骨》
阴:就是说于老早期的路子很正。
沈:是的,而且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是的东西,这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很难得,也是个时代的产物,地域文化的产物。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学校停课,1937年毕业后教书刚一年的于希宁就回到了山东。

《林和靖咏梅诗意》
阴:于老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山东工作、生活了,他后来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沈:回到山东以后,开始是回到家乡潍坊,参与同志画社的一些活动。他的老师丁东斋是同志画社的。当时的地方文人都在里面,就是一个民间社团,演一些抗日的剧目,像《放下你的鞭子》等,表现知识分子抗日的热情和对侵略者入侵的一种悲愤与反抗,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后因引起日伪的注意,于30年代末转青岛教书。到青岛后,他的画落款就签作“平寿外史”。刚去的时候当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后来在山东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做绘图工作。那时候农学院没有什么美术系,就在园艺系画各类花卉植物,用作教学方面的挂图标本。潍县比青岛解放早,有很多地下党工作者从潍坊来青岛活动,丁东斋的女儿女婿都是当时很重要的地下党的干部。青岛解放前夕,于老与一帮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一起,画漫画、写标语、散传单,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迎接青岛的解放。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采访文章——《于希宁与山大》,就是当时于老在山大农学院期间的一些经历。新成立后,于希宁调到济南,参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的组建和教学工作。

《牡丹修竹》
阴:当时是1950年,就是现在的山东艺术学院吗?
沈:不,是山东师范学院美术系。新成立后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他省份基本上没有高等美术教育。山东师范学院设立美术系,于老他们是批教师和领导,是山东高等美术教育的代开拓者和学科创建者。当时办学条件艰苦,教课不在学校里面,在营盘街找个地方先办起来。后来就发展成山东师范学院美术专修科,1958年从山师分离出来成立了山东艺专,再后来就是山东艺术学院。于老一直在山艺教书和工作,见证并亲历了学院的创建、发展、成长和壮大。

《墨梅》
阴:这期间的社会环境、生存环境有很大变化,比如说前后经历“文革”,后来又改革开放,这期间于老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沈:50年代是很艰难的时期,那是一个讲政治背景,讲家庭出身、成分的时代。于老出身于剥削家庭,又担任领导职位,只能在政治和业务的夹缝中谨慎地生存和默默地发展。50年代中期,他在南京艺术学院跟俞剑华老师进修美术史期间,做了大量的艺术史考察,随俞剑华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巩县石窟、南北响堂山、天龙山、黄石崖等地做石窟考察和青铜器纹样的考察,做了很多的手拓,后来与罗尗子先生合编了《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由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珍贵的手拓原件,“文革”抄家时遗失了很多,但是也幸存了一部分,今年于希宁先生百年诞辰,我主编了一套《百年希宁》大型文献集,也将这些幸存的拓本收入到第六卷中。

《大棚归来》
阴:现在看来,这些经历对他的艺术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沈:看到这些拓片,每张都极其丰富,都是用古蝉翼纸锤拓的,这些蝉翼纸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遗存。为什么他手里有这个东西,也是得益于陈介祺家藏。那些石窟浮雕拱梁或佛龛,每件都需要几十块甚上百块蝉翼纸拼接锤拓来完成,一块块锤上去,拓下来以后再对接起来。他把每件拓片都当做艺术作品来对待,件件拓本墨色分明,层层叠加,虚实相映,从中可以看到他在锤拓中的艺术思考和创造性劳动。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都是很大的帮助和支撑,文化传统基础的,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对艺术的虔诚,造就了他后来的大器晚成和艺术上的大化之境。

《色胜金衣美 甘逾玉液清》

《雪梅》

沈:对,1986年他在美术馆做个展览时提出了自己20年的工作计划。当时我也很惊奇,老头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个20年的工作计划。实际上他真工作了20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这20年计划是个大的计划,他分做前10年,后面分做两个5年,每一个阶段要干什么,都有具体的要求。他经常跟我说:“人生要有一个规划,光有规划不行,一定要有短期目标,长期规划是由短期目标来具体实施的。”1997年在美术馆做第二个展览的时候,他说:“这是我10年的一个总结,呈现给大家,请大家多批评。今天,大家给我打了很多对号,也要多给我打点问号和错号,需要大家从背后击我一掌,才能更好地进步。”1997年画展的成功,激发了先生的创作热情,他以饱满的情绪创作了大批艺术精品,人渐渐老了,但艺术上呈现了更加年轻化的倾向,进入了他衰年变法的新境界,他说:“齐白石、黄宾虹衰年变法实际上就是将身体生理上的劣势转化成为艺术创造上的优势的过程。”这是十分独到的见解,是经过自身生命体验的深刻阐释。2002年,15年过去了,他开始写《我的几点意见》,提前做一些思考和安排——将一生中创作的精品捐给,2005年在美术馆举办了“于希宁捐赠作品展”,展出的100件作品全部捐给美术馆,他在展览开幕式上说:“这是我的捐赠展,也是我的汇报展,及格不及格请大家来评判。”2006年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了“于希宁画作品捐赠展”,将60件精品捐给学校,然后又捐给山东省博物馆,还有很大一部分捐给了家乡潍坊。于老是2007年12月28日去世的,时年 95周岁。正好是20年计划全部完成的那一年,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谁也说不准,但的的确确是走完了这20年,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于老说了一句话,非常真切,非常感人。他说:“一个画家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以前画画就是个手艺,就是用来吃饭谋生的。像黄宾虹这样的大画家,都是布衣终生,生活上非常俭朴,现在好像艺术值钱了,画家也受人尊重了,实际上是时代的原因,要感恩这个时代,感恩祖国和人民。”

阴:所以他的感恩不是流于形式,是发自内心之中的。
沈:一个艺术家、一个知识分子爱国是重要的。这在于老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爱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感恩,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个,感恩人民的养育,并用一生努力来践行。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于老想到的是他应该做什么。非典时期他将装裱好的十余幅画送到学校,找学校领导送给战斗在抗非典线的医护人员,抗洪救灾他将平时的积蓄二十余万元捐给灾区人民。于老作为一个的知识分子,对于、人民、时代所体现的那种热情,是留给社会和后人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其实很多画家也会有这种情怀,我记得李苦禅曾经说过“所谓人格,爱国”。于老常说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有今天,感谢、感谢时代、感谢人民。一切都应该反馈给、反馈给人民。于老1987年把家里所有的房子都捐给了家乡,用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激励亲戚晚辈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未来,不要去贪图前辈留下来的东西。对家族晚辈的要求都很严格。教育他们要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能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阴:刚才听您谈了于老的人生经历跟他绘画风格所发展的几个阶段。接下来想请您谈一下于老在美术教育方面的贡献,山东艺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当中,于老算是奠基人之一了,他主要的教学思想有哪些?在教学当中是如何体现的?他这些教学思想在今天山东艺术学院是不是还有很深的痕迹?
沈:与山艺的校训一样,可以用“闳约深美”来概括。于希宁先生将闳、约、深、美提升为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博采众长为“闳”,学志精专为“约”,钻研提高为“深”,心志高远为“美”,成为培养艺术人才的教学原则和方法。“闳约深美”是蔡元培先生早提出来的,后来刘海粟到山艺,于老也让他题了“闳约深美”四个字作为学校的校训,一直延续今。

阴:于老的性格如何?请您讲讲生活中于老是怎样一个人?有哪些爱好?
沈:于老是一个特简单的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特殊的嗜好。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画家、艺术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晚年他在自序中写道:“人生短,艺术长。想做的事情太多,能做的事情太少。”特别珍惜时间,到晚没有闲的时候,要么就是写东西,要么就是读书,要么就是画画。生活上他极俭朴,鸡鸭鱼肉基本上不吃,从年轻时就不吃。他喜欢吃的就是些粗茶淡饭。喝稀饭、吃小豆腐、炒丝瓜、炒萝卜丝。他睡的床,是40年代山师的集体宿舍的木床,坐的椅子是集体宿舍的木椅,这些老家具一直陪伴了于老一生。

阴:很了不起,也就是说于老一生对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过多的奢求。
沈:是。再一点,他的时间概念特别强,他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有一次我跟他约好了去启功先生家,约好两点半去,怕路上堵车,就早走了一会儿,结果提前了20分钟,他就在楼下散步,等到差两分钟准时叩门,特别遵守时间,决不食言。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这样。

沈:他画画体现出来的也是这样,有时候画累了,他会把画放下来,先去干点别的,决不会马马虎虎去完成。一张画上的题字,他会用小纸题完了放在画上看,觉得不合适再题一个。他的大画,一定有生活的原型。他见过这个事物,跟它交流过,被它感动过,或者当时就有写生稿,或者是完全靠回忆和想象,一定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

沈:于老笔下的梅花丰富多彩,不是指梅花外表长什么样,而是艺术家赋予它的各种不同的生命形态,是意境的营造和审美理想的表达,或清、或静、或高古、或秀逸、或雄健、或苍润,画面的意境是画家创造的。看于老的画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才思,高超的笔墨能力和画面组织的本领,同时在于老的眼里,坚硬嶙峋的山石、虬劲的老石榴树,都会成为梅花的老干,而赋予它们以生命的力量。于老去世的那年,住在千佛山医院,在医院的病床上没法画画,他就在小桌上画了一套册页,取名《冰魂颂》,非常精彩。其实那时已是于老生命的一段时光了,我太太每天给他送饭,他经常突然就不认识了,问我:“那个女同志是谁?有事吗?”经我解释一番,他才恍然一笑。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侄女从河南新乡来看他,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认识了。可是他只要画起画来,才思还十分敏捷,笔下的梅花还是那么出神入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阴:就是说生命的时间,所有一切他都能忘却,唯独绘画和艺术。
沈:对,我曾为他画的《冰魂颂》写过一篇短文,冠名《冰魂颂歌》,文章的末节写道:“当一个艺术家将他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他所钟情的事业,倾注到他所喜爱的梅花里的时候,他就真成梅花了。感谢于老,让我们领悟:艺术之道,源自生命的感动和艺术家的情怀,源自一生中永不忘却的惦念。”于老七赴邓尉,四上超山,与梅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十几年后再去邓尉访梅,“惊见傲骨成狼藉”,一些老梅树被砍了,心里的那种绝望与震撼写下了“烧柴何必以檀木,煮鹤何必以琴筝”、“咬脐渴望新林生”的诗句,这种心灵的呐喊化为他永志的惦念,不断地去倾诉、去升华,表现出一种极强的韧性和坚毅,非常了不起。2002年于老90岁寿辰时自己写了一段话:“我自幼习画,不善言辞,却知道笨鸟先飞,治艺之道,靠的是勤奋和执着,不敢有丝毫懈怠。”作为他画展的前言,字里行间透出他不懈追求的艺术精神。时刻影响着你,使你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教益。

《咬定青山不放松》